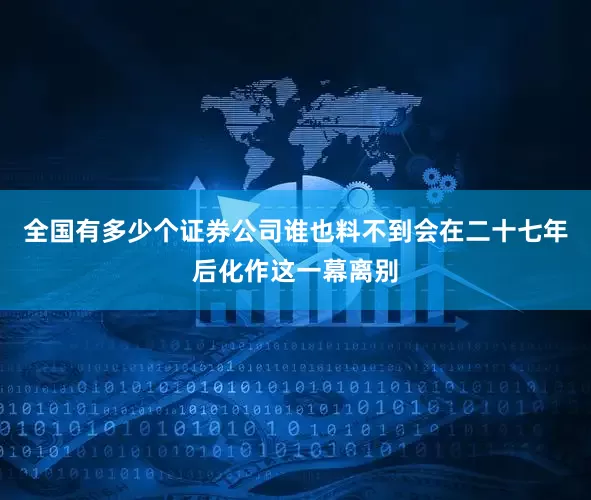
“姐,你也来了?”——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清晨,天安门广场的队伍在微雨中缓缓前行。李讷撑着一把深色雨伞,突然看见几米之外的李敏,声音有些发颤。人群里没有人开口议论,只听得到细碎的脚步声和偶尔的啜泣。李敏抬头,湿润的目光与妹妹对上,什么都没说,只是点点头,随后把伞向妹妹那边挪了挪,两个人就这样在漫长的队伍里并肩站着。
北平的初夏,谁也料不到会在二十七年后化作这一幕离别。四九年五月,西苑机场刚刚收过尘土,十岁的李敏跟着贺怡下了飞机,远远看见父亲举着手臂站在柳树下。李敏记得他那一声“娇娃”,记得被抱起时的温度。毛主席那天嘱咐她:你比讷娃大,要多照顾妹妹。这句话,被她放在心里这么多年,甚至在今天排队的间隙,仍不自觉地回响。

李讷对当年的画面没有印象,她出生时父亲已过知命之年,更多记忆停留在中南海的小院。夜深灯亮,父亲批阅文件累了,就招手让她坐腿上,或给她读《岳阳楼记》。那时李讷觉得自己拥有全世界,因为走廊那盏灯永远为她开着。李敏却常常在一旁替妹妹端茶,心里既羡又暖,她知道自己在延安保育院练出的独立,是父亲希望她拥有的本事。
搬进中南海后,姐妹俩真正成了父亲的“松弛剂”。一九五〇年的某个夜晚,叶子龙悄悄把任务塞给她们:八点,把主席骗到春藕斋跳舞。两个小姑娘对视一笑,先拖着父亲去南海边散步,再不动声色把皮鞋递过去。舞场灯一亮,毛主席的舞步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笑声交织起来,孩子们围着转圈,高兴得直叫。谁能想到,这样轻松的夜晚后来竟越来越少。
日子也并非只有暖色。五一年夏,姐妹俩为“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”争得面红耳赤。父亲听完,呵呵一笑:“坏也是中国人,外国人想要他,我们还不给呢。”一句话化解了争执,却让她们第一次感到政治判断的重量。

六二年李敏怀孕,李讷隔三差五跑去菊香书屋探望。那次父亲抱外孙,忍不住弯腰细看,须发花白,却满脸慈祥。李讷悄声说:“爸爸笑得像个老小孩。”李敏点头,眼底全是柔软。
六三年,李敏举家搬出中南海。父亲忙得抽不开身,常托李讷带话、送书。李讷到兵马司街一看,姐姐做化学实验,裤腿被硫酸烫出洞,她心疼,却也佩服那股认真劲儿。
转折来得猝不及防。七一年,李讷去五七干校锻炼并草草成婚;一年后离婚消息传到北京,毛主席沉默良久,只说了一句:“讷娃的婚事太草率了。”眼圈瞬间红了。李讷不敢回京,直到七四年父亲病重才飞奔中南海。那天,毛主席摸着女儿的脸问:“为什么这么久不回来看爸爸?”李讷低头:“离了婚,怕让您失望。”父亲把手放在她肩上:“苦我懂,这回别走了。”
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,毛主席八十二岁生日。客厅久违地热闹,李敏抱着孩子,李讷端茶添水。毛主席靠在椅子上,叫一声“娇娃”,又唤一声“讷娃”。那声音今天想起来,依旧清晰。

九月九日凌晨,电话铃响,李敏被中央办公厅接进中南海。床榻上的父亲再没有呼吸,白单覆盖到胸口。她失声喊“爸爸”,手却摸到一丝冰凉。哭声里,她仍记得把妹妹的那份思念一起喊出来。守灵申请被婉拒,她便与普通群众排队,每天凌晨三点到长安街,慢慢走进灵堂。
排队的第三天,她在人潮里撞见了李讷。一把伞,两双手,什么话都堵在喉咙。到了灵堂,姐妹俩先后向遗体深鞠躬,转身时对视,泪水自然落下。李敏轻握妹妹的手,悄声说:“爸爸一直让我们好好照顾彼此。”李讷抬起头,红着眼圈点了点头。
此后很多年,每到九月九日或十二月二十六日,李敏、李讷和毛岸青总会一同到毛主席纪念堂。排队的人越来越年轻,帽檐下的神情却与当年一样庄重。工作人员偶尔认出她们,想说点什么,又都放低了声音——那毕竟是女儿们自己的私语时刻。

进入新世纪,姐妹俩都头发斑白。一二年一次座谈结束,李讷拖着李敏的手往外走,低声感慨:“姐,小时候父亲让你照顾我,现在好像换我扶你了。”李敏笑着摆手:“照顾还得相互。”两人说着笑着,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台阶,只见长安街车流滚滚,灯火映在她们的侧脸,岁月并未抹去那份姐妹情深。
对许多人而言,毛主席是一段时代记忆;对李敏和李讷而言,那首先是慈父、是家人。排队的雨夜,如今早已远去,可那把伞,那一声“姐,你也来了”,依旧停留在很多见证者心里。只要姐妹俩仍会在特定的日子出现,广东紫荆或北京香山的秋色,总像被悄悄点燃——光阴无法带走的,是血脉相连的牵挂,也是那位父亲生前最后的期盼。
2024配资-2024配资官网-在线炒股配资平台-配资炒股配资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